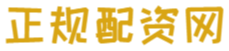
股票杠杆是什么 恒坤新材IPO:涉赌前股东与实控人配偶关联紧密,97%收入靠前五大客户引独立性质疑,会计政策突变遭监管追问
发布日期:2025-09-21 20:46 点击次数:178

2025年9月12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同意厦门恒坤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恒坤新材拟登陆科创板,计划募集资金10.07亿元。然而,公司背后潜藏的多重经营隐患股票杠杆是什么,正引发市场各方的高度警惕与强烈质疑。
2016年7月,吕某钦出资1,000万元,受让恒坤新材实际控制人易某坤手中的250万股股份,彼时这部分股份由易某坤代为持有。一年多后的2017年10月,经过勾陈资本运作,该部分股份正式过户至吕某钦名下。截至2019年6月末,吕某钦通过直接持股加他人代持的方式成为公司当时的第二大股东。
但好景不长,2020年7月,吕某钦因涉嫌非法开设赌场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这一消息本已引发市场对恒坤新材股东背景的关注,而更令人警惕的是,吕某钦及其兄弟吕某坤,与恒坤新材实际控制人易某坤的配偶陈某琴,存在着异常紧密的商业联系。
公开信息显示,陈某琴曾与勾陈资本共同参股一家企业,而这家企业的股东,正是吕某钦控股99%的厦门万人投资有限公司。不仅如此,陈某琴还曾在勾陈资本担任监事一职。
在IPO关键报告期内,恒坤新材的一项会计政策调整引发监管高度关注。2022年至2024年公司突然将引进业务的收入确认方式,从“总额法”切换为“净额法”。在上会现场,上交所对此提出问询,核心质疑聚焦两点:其一,此次变更是否严格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是否具备充分的合规依据;其二,报告期前公司长期采用“总额法”核算,为何在IPO申报的关键阶段突然调整,原因尚未明确。
值得注意的是,会计政策调整的背后,是公司盈利结构对引进产品的深度依赖。尽管近年来自产产品收入占比略有上升,但从盈利贡献来看,引进产品仍是绝对核心。数据显示,2022至2024年,公司自产产品对主营业务毛利的贡献占比从17.95%提升至34.14%,而引进产品的毛利贡献占比虽从82.05%降至65.86%,但始终占据六成以上份额,是支撑公司利润的关键支柱。
更令人担忧的是客户结构。据公司招股书披露,2022年至2024年,公司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收入占比分别达到99.22%、97.92%和97.20%,连续三年维持在97%以上的超高比例,这意味着公司几乎所有营收都系于这五家客户。
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起,韩国SKMP终止了与恒坤新材的部分产品引进合作,直接导致客户A1中止了从恒坤新材引进光刻材料的订单,改为直接向SKMP采购。这一变化对恒坤新材的2025年上半年业务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前重要股东涉开设赌场罪,实控人配偶与其关联隐秘
2021年2月,彼时仍以“恒坤股份”之名在新三板挂牌的恒坤新材(现名),曾发布公告称,公司股东吕某钦持有的2,144.91万股被司法冻结,这部分股份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9.4445%。这则看似常规的股权冻结公告,日后随着更多信息披露,逐渐牵出一段与刑事犯罪相关的股东历史,更暴露出公司实际控制人配偶与涉事股东的的隐秘关联。
招股书披露,吕某钦被冻结的股份后续处置结果进一步揭开事件复杂性:其1,664.9088万股股份被司法划转至国有全资单位淄博金控名下,剩余480万股则经山东省泰安仲裁委员会裁决,确认系吕某钦为郭某菲代持。股权的司法划转与代持认定,背后均指向同一核心原因——吕某钦涉嫌开设赌场罪。
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披露,2015年1月,吕某钦(另案处理)与陈超全、何玉琪等人合谋,由陈超全牵头组建技术团队开发手机APP,该APP可直接跳转至境外赌博网站,供用户参与网络赌博活动。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检察院已就此事正式提起公诉,指控吕某钦犯开设赌场罪。
股权代持的层层嵌套、资金往来的错综复杂,让吕某钦涉赌的犯罪阴影,悄然渗透到恒坤新材的股东结构中。回溯股权轨迹,2016年7月,吕某钦拿出1,000万元,从公司实际控制人易某坤手中受让250万股股份,当时这笔股权并未直接登记在吕某钦名下,而是由易某坤本人代为持有。一年多后的2017年10月,经过勾陈资本运作,这250万股才正式过户至吕某钦名下。
但股权代持的故事并未就此终结。2019年5月,李某江以每股10元的价格认购恒坤新材550万股股份,其中483.29万股的资金直接来自吕某钦关联账户——实为吕某钦委托代持。直至2021年6月,李某江才按原价转让该部分股份,并上缴相关资金,这一代持关系才正式解除。
比股权代持更令人警惕的,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易某坤的配偶陈某琴,与吕某钦、吕某坤兄弟之间若隐若现却又真实存在的商业关联。
天眼查显示,陈某琴曾在勾陈资本担任监事一职,这一任职直至2021年10月才退出,而勾陈资本正是此前协助吕某钦完成250万股股权过户的关键主体。不仅如此,2017年5月,陈某琴还与勾陈资本一同入股厦门万人投资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由吕某钦持股99%绝对控股,是其核心关联企业;2018年6月,陈某琴悄然退出该公司股东行列。
收入确认政策突变引监管追问,“总额法”改“净额法”疑云难消
2025年7月25日,科创板上市委一纸“暂缓审议”决定,给恒坤新材的IPO进程按下“暂停键”。在当天的上会审议现场,上市委明确提出两大质疑:其一,此次收入确认政策变更是否严格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是否具备充分、合规的依据;其二,报告期前公司长期以“总额法”核算引进业务收入,为何在IPO申报的关键节点突然切换为“净额法”,变更的合理性何在。
以2024年数据为例,若沿用“总额法”,恒坤新材引进产品销售收入可达6.36亿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64.89%,是无可争议的收入主力;但切换至“净额法”后,该项收入骤降至1.96亿元,占比仅剩下36.23%。数字调整的背后,是公司收入结构的“表面重塑”——报表上,主要收入来源从“引进产品”摇身变为“自产产品”,业绩结构看似实现显著“优化”。
但纸面数字的“光鲜”,终究掩盖不了公司盈利对引进产品的“深度绑定”。2022至2024年,恒坤新材主营业务毛利率中,自产产品贡献毛利占比虽从17.95%提升至34.14%,但引进产品的毛利贡献占比即便从82.05%降至65.86%,牢牢占据六成以上份额,仍是支撑公司利润的“压舱石”。
前五大客户撑起97%收入,客户集中风险引爆业绩危机
作为主攻集成电路关键材料的企业,恒坤新材主打光刻材料与前驱体材料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本应在技术创新与市场拓展上展现竞争力。但现实是,其客户结构的极度集中问题,已成为市场与监管审视的焦点,公司几乎将所有经营“赌注”压在前五大客户身上,一旦客户合作生变,经营根基便面临动摇风险。
2022年至2024年,恒坤新材的营收数据看似呈现增长态势:营业收入从3.22亿元攀升至5.48亿元,复合增长率达19.2%;扣非净利润分别为9,103.53万元、8,152.78万元、9,430.36万元,复合增长率为1.18%。
但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却隐藏着极为脆弱的经营逻辑——同期,公司来自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收入分别为3.15亿元,3.53亿元、5.25亿元,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竟分别达到99.22%、97.92%和97.20%。连续三年维持在97%以上的客户依赖度。
如今,“客户变动”的风险已从担忧变为残酷现实。2022至2024年间,恒坤新材向客户A1销售的光刻材料(该产品引进自韩国SKMP),是公司实打实的“利润奶牛”,这部分业务分别贡献1.38亿元、1.16亿元和1.42亿元销售毛利。
但2025年初,这一核心利润来源突然“断供”——韩国SKMP宣布终止与恒坤新材的部分产品引进合作,转而直接向客户A1销售相关光刻材料,彻底绕开了恒坤新材这一中间环节。
合作终止的冲击很快传导至业绩端,效果立竿见影。在交易所第二轮问询中,恒坤新材不得不公开承认,2025年1-6月,公司向客户A1销售的引进光刻材料,其收入、毛利及在手订单均出现“大幅下降”,且已对短期经营业绩“造成了不利影响”。
面对业绩压力,恒坤新材辩解称,其他自产与引进产品的销售收入有所增长股票杠杆是什么,能够“一定程度”抵消客户A1订单流失的冲击。
